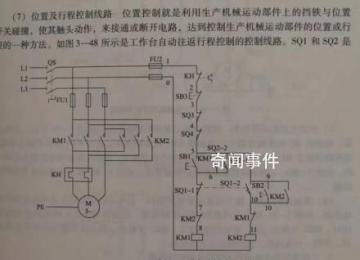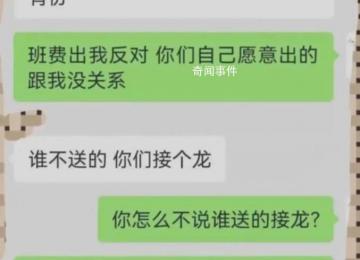當(dāng)?shù)妄g老人照顧高齡老人 老年子女困在父母病床前
導(dǎo)讀:又是凌晨。兩點(diǎn)多,張偉國(guó)被一陣慘叫聲驚醒。他顧不上穿拖鞋,跌跌撞撞沖進(jìn)父親房間。房門打開的剎那,惡臭撲面而來(lái)。看見兒子闖入,父親像

又是凌晨。兩點(diǎn)多,張偉國(guó)被一陣慘叫聲驚醒。
他顧不上穿拖鞋,跌跌撞撞沖進(jìn)父親房間。房門打開的剎那,惡臭撲面而來(lái)。看見兒子闖入,父親像是做了壞事的小孩,迅速用被子蓋住了床上的排泄物。
張偉國(guó)沉默著,與父親四目相對(duì)。后者突然大喊,“你們要害我,我不認(rèn)識(shí)你們。”
張偉國(guó)情緒有些失控。他開始扇自己的耳光,一個(gè)巴掌接一個(gè)巴掌打在臉上。
不知道抽了多少下,他冷靜下來(lái),戴上口罩,熟練地把污穢物收拾干凈,將父親背入浴室。趁著父親洗澡間隙,他趕緊打掃房間,噴灑空氣清新劑。
父親洗完澡,已經(jīng)凌晨三點(diǎn)半了。老人沒去睡覺,而是打開電視,對(duì)著一個(gè)購(gòu)物頻道看得津津有味。張偉國(guó)在一旁氣得全身哆嗦,可他沒辦法——那畢竟是他的父親。
張偉國(guó)63歲,父親85歲。自從兩年前,父親患上阿爾茨海默病后,他就被父親困住了。沒有人能幫張偉國(guó)分擔(dān)。他的母親、妹妹很早就去世了。妻子和女兒原本能搭把手,可自從父親總在家裸奔后,母女倆便很少登門了。
日漸衰老的身軀,讓張偉國(guó)有時(shí)也力不從心。這兩年,他除了頭暈乏力外,走路時(shí)也總會(huì)雙腿發(fā)軟,有時(shí)還會(huì)伴隨劇烈疼痛,得好一會(huì)兒才能緩過來(lái)。為了照顧父親,他已經(jīng)連續(xù)兩年沒有體檢了。
偶有空閑,他會(huì)給幾個(gè)老伙計(jì)打視頻電話——但各自家里都有老人要照顧,往往說不上幾句話。張偉國(guó)發(fā)現(xiàn),越來(lái)越多像他一樣的“低齡老人”,需要照顧更加年邁的父母。
2月11日第三屆中國(guó)人口與發(fā)展論壇上,《中國(guó)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響因素跟蹤調(diào)查(2021年)》發(fā)布結(jié)果發(fā)布顯示,我國(guó)已經(jīng)進(jìn)入長(zhǎng)壽時(shí)代,2020年全國(guó)百歲老人11.9萬(wàn)人,2021年人均預(yù)期壽命78.2歲,到2050年,80歲以上老人數(shù)量將翻兩番。另一方面,來(lái)自國(guó)家衛(wèi)健委老齡健康司的數(shù)據(jù)顯示,截至2021年,我國(guó)失能、半失能和失智老人已達(dá)4500萬(wàn)。北京大學(xué)一項(xiàng)人口學(xué)研究顯示,到2030年,我國(guó)失能老人規(guī)模將超過7700萬(wàn)。
這意味著,“老人照顧老人”可能成為每個(gè)家庭不得不面對(duì)的養(yǎng)老困局。
“拋開孝道和倫理的話,很多人會(huì)活在殘酷與絕望中。”張偉國(guó)說。
被困
父親張大均總會(huì)做一些讓張偉國(guó)尷尬又不知所措的事。比如趁他沒注意,搶走別比人的東西;又或者,突然抱住路過的女性。這些“為老不尊”的行為,沒少讓張偉國(guó)挨罵,甚至因此驚動(dòng)過警察。警察到現(xiàn)場(chǎng)看了,批評(píng)張偉國(guó)幾句,讓他好生照看老人。
于是外出遛彎,他得緊跟在顫顫巍巍的父親后面,生怕老人離開自己視線。
在這個(gè)鬧市區(qū)的工廠家屬院里,鄰居們知道張大均老年癡呆,見到他都繞著走。
張大均以前可不這樣。退休前,他是廠里的工程師。妻子去世幾年后,他找了個(gè)老太太當(dāng)女朋友,同居,彼此有個(gè)照應(yīng)。在外人看來(lái),張大均是個(gè)“挺獨(dú)立樂觀的老頭”。彼時(shí),張偉國(guó)和妹妹的工作都不錯(cuò),倆人從未擔(dān)心過父親的養(yǎng)老問題。
平日里,兄妹倆不管誰(shuí)有時(shí)間,都會(huì)去陪父親坐會(huì)兒,日子平靜且閑適。
2020年,是張偉國(guó)退休前的最后一年。他天天幻想著退休后的生活——和妻子到處旅行,也可以再上個(gè)老年大學(xué)。他還專門學(xué)了駕照,準(zhǔn)備和年輕人一樣開著車?yán)僳E天涯。
也就是在那個(gè)時(shí)間段,妹妹突然車禍去世。張偉國(guó)馬上意識(shí)到,以后只有自己照顧父親了。下半年的一天,父親的女友打來(lái)電話,說老張最近總是目光呆滯、健忘,性格變得異常暴躁,還整宿整宿看電視。
張偉國(guó)沒太在意,他覺得父親可能只是年紀(jì)大了。
2021年1月,張偉國(guó)正式退休。退休后,他和妻子外出玩了一圈。回家后,他去看父親。老人表現(xiàn)很正常,女朋友在一旁胡亂收拾著屋子。他陪父親在沙發(fā)上坐著,老人突然冒出一句,“你媽去買菜了,怎么還不回來(lái)?”
“我媽都去世十幾年了,你糊涂了吧!”張偉國(guó)有些詫異。話音沒落,父親抓起茶幾上的杯子摔得粉碎,用極為難聽的話辱罵兒子。到了中午吃飯的時(shí)候,他又對(duì)張偉國(guó)說,“你叔下午過來(lái)找我辦事,你吃完飯就回去吧。”
張偉國(guó)徹底聽蒙了——他唯一的叔叔,早就過世了。
午休過后,張大均看上去又恢復(fù)了正常。張偉國(guó)看著沒事,就回家了。回到家,他講起父親的異常表現(xiàn)。“我爺爺不是老年癡呆了吧?”女兒說。張偉國(guó)趕緊讓她在網(wǎng)上搜了些資料,比對(duì)下來(lái),他覺得父親的確有了點(diǎn)兒阿爾茨海默病的前兆。
之后的日子,像是有一個(gè)看不見的橡皮擦不斷抹去老人的記憶,他有時(shí)完全不認(rèn)識(shí)兒子,有時(shí)偶爾記起有個(gè)女兒,但不相信她已經(jīng)去世。張偉國(guó)帶父親去醫(yī)院檢查,他很快被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病。醫(yī)生開了些改善認(rèn)知功能和控制精神癥狀的藥物,讓他們回家了。
醫(yī)生告訴張偉國(guó),這個(gè)病只會(huì)越來(lái)越嚴(yán)重,病人需要人全天陪護(hù),日常再做些智能和社交方面的訓(xùn)練,不能整天關(guān)在屋子里。
他把父親的情況告訴了他的女友。老太太很冷靜,要了一萬(wàn)元“感情損失費(fèi)”后,頭也沒回地離開了。當(dāng)房間只剩張偉國(guó)父子倆時(shí),他徹底明白,自己被困住了。
妻子迅速表態(tài)說和他一起分擔(dān)照顧老人的重任。但張大均太能折騰了,亂發(fā)脾氣、罵人不說,還動(dòng)不動(dòng)脫光衣服亂跑,漸漸的,妻子和女兒便不再登門了。
張偉國(guó)成了唯一照顧父親的人。退休前,他朝九晚五,早睡早起。現(xiàn)在他沒有固定作息,父親做什么,他就只能做什么,經(jīng)常熬了一個(gè)晚上,還沒睡幾個(gè)小時(shí),父親就又起床進(jìn)入了自己的世界。張偉國(guó)只能跟著一起起來(lái)。
他知道自己也在不可避免地衰老著——血壓忽高忽低,呼吸偶爾急促;有時(shí)特別想上廁所,站在馬桶前,卻要半天才能尿出來(lái)。
張偉國(guó)用父親的退休金陸續(xù)請(qǐng)過幾個(gè)保姆,但保姆們受不了張大均裸奔,紛紛離開。張偉國(guó)還想過把父親送到專門收治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養(yǎng)老院,但出于孝道,他打消了這個(gè)念頭。
困在時(shí)間里的張大均,記憶還在不斷消失——他先是忘掉了近幾年的事,接著又忘了近十幾年的事。到了今年,他只能記住些自己三四十歲時(shí)的生活片段。他也從不認(rèn)為自己病了,一切來(lái)自兒子的關(guān)懷,都讓他覺得是在加害自己。
“那是我爸,無(wú)論指責(zé)、謾罵,我都要忍下來(lái)。”張偉國(guó)知道這是愚孝,可他沒得選。
“如果可以安樂死”
張偉國(guó)也想過一些“如果”——如果父親在睡夢(mèng)中去世就好了,如果經(jīng)歷一場(chǎng)意外也行。每到這些念頭沖上來(lái)的時(shí)候,他就覺得自己不配做人。而父親再度暴躁、折騰后,“如果”又會(huì)出現(xiàn)。并且,這種渴望來(lái)得直接而強(qiáng)烈。
“長(zhǎng)期壓抑的家庭看護(hù)者,他們的壓力就像是在空杯子上慢慢加水,快到杯沿兒緣處,似乎還能承受,等到再滿上,壓力就如同杯中的水滿溢出來(lái),崩塌殆盡。”日本一本叫《看護(hù)殺人》的書中,記錄了不少家庭看護(hù)者的普遍困境。
這種困境對(duì)66歲的常桂英來(lái)說再熟悉不過,而類似張偉國(guó)那些“如果”的念頭,也在她的腦海中不只一次出現(xiàn)過。
常桂英的母親88歲了。6年前,她在小區(qū)遛彎時(shí),被一輛飛馳的電動(dòng)車撞倒,頭部受了重傷,成了植物人。醫(yī)院診斷她是“彌漫性軸索損傷”,屬于比較嚴(yán)重的顱腦損傷。即便能幸存,也是嚴(yán)重失能或植物人狀態(tài)。
“我母親最終活了下來(lái)。”常桂英從醫(yī)生那里得知,母親一年內(nèi)醒不過來(lái)的話,就是植物人了。那之后,她按月數(shù)著,在醫(yī)院過完了12個(gè)月。這12個(gè)月,她幾乎沒有離開過醫(yī)院。
陪在母親床窗邊,常桂英一直對(duì)她講話。講累了,就用手機(jī)小聲播放河北梆子片段,但母親從沒做出過一個(gè)動(dòng)作,安靜得如一株植物。
12個(gè)月過后,常桂英將母親接回了家。她拿出自己記的賬本一看,母親在醫(yī)院的這一年,共花費(fèi)了22.4萬(wàn)元,其中5萬(wàn)是肇事方出的。常桂英薪水不高——上班時(shí)月薪4000多,退休了只有2000多,夫妻倆少量的存款原本是留著給兒子結(jié)婚用的,現(xiàn)在都花在了母親身上。為了減輕家里的經(jīng)濟(jì)負(fù)擔(dān),已經(jīng)退休的丈夫在小區(qū)當(dāng)起了保安。
母親有一套小房子,常桂英和丈夫商量后,自己搬了過去。從此,她徹底沒有私生活了。
原本,她和丈夫都愛跳舞。母親成為植物人后,她一次都沒再跳過,甚至連想一下的心思都沒有。每天早上6點(diǎn)多,她得起來(lái)給母親做早餐。等待早餐做好的時(shí)間里,她用溫水浸泡毛巾,為母親擦臉、擦手,再用消毒棉簽,蘸著漱口水清理口腔。接著,她把飯菜湯混在一起倒入榨汁機(jī),打成糊狀,再通過注射器打到母親的胃管里。
胃管是從鼻腔插入,置于胃部,醫(yī)學(xué)術(shù)語(yǔ)叫“鼻飼”。
常桂英的“鼻飼”技術(shù)是在醫(yī)院學(xué)會(huì)的。她每次給母親喂飯,都會(huì)先注入少量溫開水,喂完飯,再用溫開水沖洗胃管。“不管是食物,還是湯水,溫度太冷、太熱都不行。”常桂英每天要這樣喂三次。每次“鼻飼”,還得將床搖成45度角。否則食物反流,容易造成肺部感染。
看似繁瑣的喂飯過程,對(duì)常桂英來(lái)說已經(jīng)是日常護(hù)理中最簡(jiǎn)單的操作了。
為了不總洗床單,她給母親穿了尿不濕,每隔一會(huì)兒就要檢查下。一旦皮膚被尿液浸泡,容易發(fā)生潰爛。排便則比較麻煩,“她不會(huì)表達(dá),經(jīng)常弄得的滿床都是”,常桂英說,幾乎每個(gè)植物人的房間,都會(huì)有糞便的殘留臭味。
“什么也做不了,人生就這樣消耗著。”這些年,常桂英錯(cuò)過了很多事情。比如在微信群,她看到之前的同事旅游、聚餐、跳舞時(shí),自己只能偷偷落淚。再比如,兒子帶女朋友見家長(zhǎng)時(shí),常桂英只讓他們見了丈夫;兒子結(jié)婚當(dāng)天,她在婚禮現(xiàn)場(chǎng)待了1個(gè)小時(shí),就匆匆回去照顧母親了。
親家總叮囑自家女兒,多心疼婆婆,沒事去看看老太太。可常桂英不想讓他們過來(lái)。因?yàn)橛幸淮危牭絻合毙÷曊f,“姥姥家怎么總是有一股臭味。”
常桂英知道兒媳婦沒惡意,但她寧可只有自己和母親,困在那個(gè)60多平米的家屬樓的房間中。
“我經(jīng)常右耳耳鳴,聽聲音總有咚咚的聲音,有時(shí)心臟會(huì)連續(xù)快速跳動(dòng),手腳麻木、冰涼,甚至?xí)查g失憶,明明很累,又整夜整夜睡不著。”常桂英知道,這是“三高”癥狀,但她沒有去醫(yī)院看。兒子為此沒少和她爭(zhēng)吵,她總說休息一下就好。丈夫勸常桂英把母親送到植物人托養(yǎng)機(jī)構(gòu),可她總認(rèn)為守在母親身邊更安心。丈夫知道,她其實(shí)是怕花錢。
守在母親身邊,常桂英每隔一兩個(gè)小時(shí)就得給母親翻一次身,朝一側(cè)躺的時(shí)間太長(zhǎng),容易生褥瘡。她還得不停地給母親的四肢做按摩,防止肌肉萎縮。
“我最害怕自己走在母親前面。”常桂英說,那樣的話,媽媽就沒人管了。
偶爾,她會(huì)拿著兒子送來(lái)的平板電腦追劇。她喜歡那個(gè)叫靳東的男演員,陪母親的這幾年,都是靳東的劇在陪著她。不管是《偽裝者》《我的前半生》,還是《精英律師》和《底線》,常桂英都能說出每集的具體情節(jié)。有時(shí),她會(huì)把平板放在母親身邊,希望母親也能喜歡靳東。
隨著劇集一遍遍地的播出與結(jié)束,常桂英不得不回到現(xiàn)實(shí)——現(xiàn)實(shí)里的她,對(duì)著母親嘆氣、發(fā)呆,一遍遍念叨各個(gè)親戚的是與非。母親無(wú)法回應(yīng),常桂英越來(lái)越疲憊。每到這個(gè)時(shí)候,她會(huì)和張偉國(guó)一樣,想到“如果”。
如果中國(guó)能放開安樂死就好了,常桂英覺得,雖然聽著不孝順,至少大家都能解脫。她把這個(gè)想法告訴過丈夫。丈夫說,“你胡說啥呢?我們年紀(jì)再大,也得照顧老人。況且,咱們就這一個(gè)老人了。”
每每這時(shí),常桂英便不再說話。她日復(fù)一日盯著床上的母親。她覺得自己好歹是一株鮮活的植物,母親這株植物卻枯萎了。
去年6月,家里多了個(gè)小孫女。常桂英很高興,但她至今才見過孫女幾次。她不讓兒子把孫女帶來(lái),擔(dān)心床上骨瘦如柴的老人嚇壞孩子。
這段時(shí)間她總勸兒子再要一個(gè)孩子,“你看你姥姥的情況,一個(gè)孩子根本不行的,人都有老的那一天。”
“人一老,大概率就沒人喜歡了”
按照這種“養(yǎng)兒防老”的思路,89歲的何金忠不存在太多養(yǎng)老困境——他有1個(gè)兒子、3個(gè)女兒,看起來(lái)足以照顧一個(gè)年邁的父親。他本身還算健康,沒有老年癡呆,也沒特別麻煩的病癥,只是單純因?yàn)槟昙o(jì)大了,獨(dú)自生活不大方便,尤其是在較為偏遠(yuǎn)的鄉(xiāng)下。
早些年,妻子去世后,兒子何書文提過讓父親到城里生活。何金忠怕給子女添麻煩,也擔(dān)心自己適應(yīng)不了城里的生活,拒絕了。2022年12月,他在老家感染了新冠,兒子把他接進(jìn)城,讓他不要再回鄉(xiāng)下了。
何金忠就此留了下來(lái)。
他的四個(gè)子女中,何書文年紀(jì)最大,68周歲,退休前是一名教師。3個(gè)女兒,年紀(jì)最小的今年也有60歲了。何書文原本想著,老父親住在自己家里,3個(gè)妹妹沒事時(shí),可以過來(lái)照顧下。如果父親生病住院,大家各盡所能。妹妹們嘴上應(yīng)允了。
何金忠新冠康復(fù)后,身體也一直虛弱。平日里,何書文會(huì)給父親喂飯、喂藥,天氣好的時(shí)候,用輪椅推著他下去曬太陽(yáng)。幾個(gè)月下來(lái),他發(fā)現(xiàn),幾個(gè)妹妹很少過來(lái)看老人。偶爾過來(lái)幾次,都還會(huì)抱怨大哥沒有照顧好父親。
何書文起初不在意所謂的指責(zé),可次數(shù)多了,他委屈起來(lái),“明明我照顧得很好,為什么挑毛病?”這種情緒感染到了妻子和孩子,一家三口關(guān)起門來(lái)吐槽——妻子說,老父親是鄉(xiāng)下人,沒有退休金,在城里的開銷都要靠他們夫妻倆的退休工資,“幾個(gè)妹妹一分錢沒給過不說,還總說風(fēng)涼話”。這些吐槽在房門打開后銷聲匿跡,大家維系著表面的和諧。
矛盾終于在2023年春節(jié)爆發(fā)了。
春節(jié)前,何金忠在家摔了一跤,髖部骨折。由于他年紀(jì)大了,本就骨質(zhì)疏松,醫(yī)生建議他至少住院一個(gè)月,到時(shí)候看情況再?zèng)Q定是否繼續(xù)住院。
老人住院后,自然需要有人陪伴。按照何書文的預(yù)想,自己和3個(gè)妹妹每人陪護(hù)一周。住院費(fèi)除了新農(nóng)合報(bào)銷外,剩下的費(fèi)用平攤。
但三個(gè)妹妹分別只陪護(hù)了一天,就離開了。
每個(gè)人都給出了充分的理由——大妹說自己“三高”不能熬夜,二妹稱要回去照顧婆婆,三妹必須帶孫子。三人臨走時(shí),何書文說,自己可以多負(fù)擔(dān)一點(diǎn),但還是希望她們能規(guī)劃出些時(shí)間來(lái)。之后幾天,何書文每天泡在醫(yī)院,連除夕都沒回家。過年那幾天,三個(gè)妹妹倒是分別來(lái)醫(yī)院待了會(huì)兒,但每個(gè)人都沒超過半天。
何書文自己的身體也不好。他有糖尿病,平時(shí)格外注意。父親住進(jìn)醫(yī)院后,不規(guī)律的生活和飲食導(dǎo)致他雙腿麻木不聽使喚,后來(lái)又出現(xiàn)了心慌、胸悶、胸痛等癥狀。他做了檢查,醫(yī)生說是“糖尿病引發(fā)的心血管病變”。”
身體狀況突變后,何書文再次提出希望妹妹們可以分擔(dān),但她們也再次以各種理由推脫。
何書文的妻子顯然不太高興。一開始,她還在醫(yī)院幫忙,看到三個(gè)妹妹不去,她也不去了。夫妻倆為此吵過幾次。一次吵完,何書文直接到住院處,將上面家屬的聯(lián)系方式,更換成了三個(gè)妹妹的電話,自己回家睡覺去了。
他本想通過這種方式,倒逼三個(gè)妹妹陪父親。可才回家兩個(gè)小時(shí),醫(yī)院電話打過來(lái)了,“你們家里怎么回事,咋一個(gè)人都找不到?”何書文趕緊去了醫(yī)院。后來(lái)他從父親那里得知,大妹妹的確來(lái)了醫(yī)院,可沒待一會(huì)兒就走了。
妹妹離開醫(yī)院時(shí),又去住院處,將聯(lián)系電話變更為大哥的。
何書文憤怒地把三個(gè)妹妹叫到醫(yī)院。兄妹四人在父親的病房里翻舊賬,妹妹們表述的大概意思是,何書文是家里唯一的男孩,父親的財(cái)產(chǎn)都會(huì)由他繼承——所謂遺產(chǎn),就是老家一處舊宅子,和幾千元存款。接著,她們把父親對(duì)兒子的好、對(duì)女兒的壞,羅列了一遍。
躺在床上的父親始終沒有說話,只是木然地看著沒有打開的電視機(jī)。
爭(zhēng)吵了幾個(gè)小時(shí)后,三個(gè)妹妹集體決議,“不出錢,盡量出力”。何書文知道,這個(gè)“盡量”是空頭支票。那之后,妹妹們果然再也沒去過醫(yī)院,甚至連電話都不打了。
何書文沒辦法,只能自己每天出入醫(yī)院。值班護(hù)士看到他,有些驚訝,“你都這么大年紀(jì)了,沒人替你班嗎?”何書文都尷尬地回答,“她他們忙,她他們忙。”
他沒想過這樣的日子要繼續(xù)多久,他覺得只要盡到一個(gè)孩子的本分就行了。經(jīng)過這次的事情,何金忠倒是看明白了不少,他說不想活太久了,“人一老,大概率就沒人喜歡了,在這方面,很多人都是自私的。”
-
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(hào)禁止網(wǎng)民評(píng)論2023-09-16 16:51:09近日,深圳市交通運(yùn)輸局對(duì)網(wǎng)民申請(qǐng)公開北極鯰魚調(diào)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(fù),很快便引起了社會(huì)大眾對(duì)于5個(gè)月前,深圳市交通運(yùn)輸局將及
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(hào)禁止網(wǎng)民評(píng)論2023-09-16 16:51:09近日,深圳市交通運(yùn)輸局對(duì)網(wǎng)民申請(qǐng)公開北極鯰魚調(diào)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(fù),很快便引起了社會(huì)大眾對(duì)于5個(gè)月前,深圳市交通運(yùn)輸局將及 -
 軍訓(xùn)順拐同學(xué)們組成了方隊(duì) 引發(fā)了網(wǎng)友們的熱議2023-09-16 16:49:42軍訓(xùn)順拐同學(xué)們組成了方隊(duì)近日,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(xùn)場(chǎng)上,一幕引人注目的場(chǎng)景吸引了網(wǎng)友們的目光,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(duì)的隊(duì)伍。這支
軍訓(xùn)順拐同學(xué)們組成了方隊(duì) 引發(fā)了網(wǎng)友們的熱議2023-09-16 16:49:42軍訓(xùn)順拐同學(xué)們組成了方隊(duì)近日,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(xùn)場(chǎng)上,一幕引人注目的場(chǎng)景吸引了網(wǎng)友們的目光,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(duì)的隊(duì)伍。這支 -
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(lái)就心慌2023-09-16 16:45:25或許你聽說過,有人因?yàn)楣ぷ魈β刀箲],也聽說過有人因?yàn)楣ぷ魈y而焦慮,但如今,越來(lái)越多的人,正因?yàn)榭臻e而焦慮。尤其是在一種內(nèi)卷加
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(lái)就心慌2023-09-16 16:45:25或許你聽說過,有人因?yàn)楣ぷ魈β刀箲],也聽說過有人因?yàn)楣ぷ魈y而焦慮,但如今,越來(lái)越多的人,正因?yàn)榭臻e而焦慮。尤其是在一種內(nèi)卷加 -
 網(wǎng)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(wàn) 遂依法對(duì)其開展了稅務(wù)檢查2023-09-16 16:38:53據(jù)國(guó)家稅務(wù)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(qū)稅務(wù)局網(wǎng)站消息,前期,廣西壯族自治區(qū)稅務(wù)部門通過分析發(fā)現(xiàn)網(wǎng)絡(luò)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,經(jīng)提示提醒、督促整改
網(wǎng)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(wàn) 遂依法對(duì)其開展了稅務(wù)檢查2023-09-16 16:38:53據(jù)國(guó)家稅務(wù)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(qū)稅務(wù)局網(wǎng)站消息,前期,廣西壯族自治區(qū)稅務(wù)部門通過分析發(fā)現(xiàn)網(wǎng)絡(luò)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,經(jīng)提示提醒、督促整改 -
 恒大人壽嚴(yán)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(fēng)險(xiǎn)處置再進(jìn)一步2023-09-16 16:37:30恒大人壽風(fēng)險(xiǎn)處置再進(jìn)一步。9月15日,國(guó)家金融監(jiān)督管理總局深圳監(jiān)管局官網(wǎng)公布《關(guān)于海港人壽保險(xiǎn)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(xiǎn)有限公司保
恒大人壽嚴(yán)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(fēng)險(xiǎn)處置再進(jìn)一步2023-09-16 16:37:30恒大人壽風(fēng)險(xiǎn)處置再進(jìn)一步。9月15日,國(guó)家金融監(jiān)督管理總局深圳監(jiān)管局官網(wǎng)公布《關(guān)于海港人壽保險(xiǎn)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(xiǎn)有限公司保 -
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(guān)注和熱議2023-09-16 16:35:03在最近的一場(chǎng)演出中,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。然而,當(dāng)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(shí),王耀慶卻因?yàn)楸瘋?
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(guān)注和熱議2023-09-16 16:35:03在最近的一場(chǎng)演出中,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。然而,當(dāng)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(shí),王耀慶卻因?yàn)楸瘋? -
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(wǎng)站列入專項(xiàng)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(quán)的又一次挑釁2023-09-16 16:33:55據(jù)塔斯社15日?qǐng)?bào)道,對(duì)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(wǎng)站將朝鮮國(guó)務(wù)委員長(zhǎng)金正恩列入專項(xiàng)人員名單,俄副外長(zhǎng)加盧津批評(píng)稱,這是基輔政權(quán)的又一次
金正恩被烏克蘭網(wǎng)站列入專項(xiàng)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(quán)的又一次挑釁2023-09-16 16:33:55據(jù)塔斯社15日?qǐng)?bào)道,對(duì)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(wǎng)站將朝鮮國(guó)務(wù)委員長(zhǎng)金正恩列入專項(xiàng)人員名單,俄副外長(zhǎng)加盧津批評(píng)稱,這是基輔政權(quán)的又一次 -
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-09-16 16:32:26據(jù)荔枝新聞報(bào)道,近日,在G2610次高鐵上,一女子座位被占,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。當(dāng)事人李女士介紹,換回座位后,對(duì)方多次對(duì)其座椅進(jìn)行敲
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-09-16 16:32:26據(jù)荔枝新聞報(bào)道,近日,在G2610次高鐵上,一女子座位被占,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。當(dāng)事人李女士介紹,換回座位后,對(duì)方多次對(duì)其座椅進(jìn)行敲 -
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(wàn)2023-09-16 16:29:35前期,重慶市稅務(wù)部門通過分析發(fā)現(xiàn)袁冰妍存在涉稅風(fēng)險(xiǎn),經(jīng)提示提醒、督促整改、約談警示后,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,加之其關(guān)聯(lián)企業(yè)存在偷逃稅
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(wàn)2023-09-16 16:29:35前期,重慶市稅務(wù)部門通過分析發(fā)現(xiàn)袁冰妍存在涉稅風(fēng)險(xiǎn),經(jīng)提示提醒、督促整改、約談警示后,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,加之其關(guān)聯(lián)企業(yè)存在偷逃稅 -
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(zhǔn)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-09-16 16:27:319月16日,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(xiàn)身了,這些年他一直隱身,很少曝明星大瓜了,很多網(wǎng)友紛紛表示,沒有卓偉的日子,娛樂圈真的好寂寞,明星的戀
卓偉爆料古裝劇準(zhǔn)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-09-16 16:27:319月16日,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(xiàn)身了,這些年他一直隱身,很少曝明星大瓜了,很多網(wǎng)友紛紛表示,沒有卓偉的日子,娛樂圈真的好寂寞,明星的戀